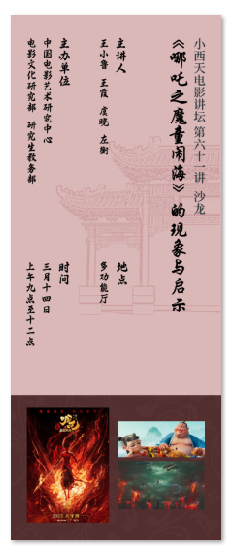
由中国电影资料馆(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)电影文化研究部与研究生教务部联合主办的学术活动——“小西天电影讲坛”第六十一讲日前举行。此次讲坛以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现象与启示为主题,由王小鲁、王霞、虞晓、左衡四位电影学者担任主讲人,从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类型创作、文化批评等多个角度出发,对该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,提出了电影中关于个体与社会、传统与现代、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多重主题,并对电影的商业成功与文化价值进行了反思。
一、共情机制与集体心理:
引发观众共鸣
四位学者一致认为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通过注入现实感和构建共情机制,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。电影通过人情和人性的描绘,构建了一个观众熟悉的世界,这种现实感使得观众,特别是青年观众,与影片中的角色实现了共情。
虞晓表示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它将现实的人情和人性注入神话故事中,让观众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情。电影中的人物关系、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,例如“考公”情节、科层化现象、成功学价值观等,都让观众感到亲切和熟悉。
他进一步解释,影片通过群像戏塑造了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,无论是仙界、妖界还是人间的群体,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种塑造不仅依赖于主创对人性的深刻理解,还体现了对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。例如,哪吒与家庭的关系展现了他对家庭关系和爱的渴望,这种渴望越强烈,他对爱的抗拒就越明显。这种情感在影片中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得以表达,如哪吒在去玉虚宫考试时拒绝母亲的拥抱,以及在玉虚宫选择用敖丙的形象见哥哥,影片中加入了日常生活的情感,使观众能够理解并接受哪吒的内心世界。
虞晓还探讨了观众为何会对电影中的角色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。他以为,影片中的一个关键场景,即八爪鱼在鼎中自食其爪并与其他生物分享这一幕,既诡异又残忍,同时又充满真诚和蠢萌。这种场景不仅让观众感到震撼和毛骨悚然,更是通过吸引力的原则,让观众记住了这些鲜活的角色。他进一步分析了仙界与妖界角色的对比,仙界的角色如鹿童和鹤童虽然完美无瑕,但缺乏人性的真实感。相比之下,妖界和底层的角色,如土拨鼠和石矶娘娘,尽管有缺陷和欲望,却显得更加鲜活和生动。这些角色不仅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冲击,更是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痛,因为这些生命尽管不完美,但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相似,具有同样的欲望和缺点。正是这种对人性和欲望的真实描绘,使得影片中的角色死亡或被消灭不再是无关痛痒的事件,而是引发了观众的同类伤感。
王小鲁接着从共情机制和文化符号的角度展开讨论。他认为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引发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大规模的共情现象,共情机制的建立主要依赖于文本的依据和流行文化元素两个方面。影片的共情机制不仅依赖于其叙事和文本,还得益于动画技术的进步和流行文化元素的融入。片中充满了类似周星驰电影和抖音文化的趣味性,这些元素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,影片中的烤鱿鱼情节与《武状元苏乞儿》中的狗饭情节相似,体现了喜剧包装下的悲剧。他还提到了中国动画技术的发展,特别是天元鼎中的2亿角色场景,不仅展示了技术的进步,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。这种大规模的场景在中国电影史上屡见不鲜,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常见的巨大规模,这些都是中国观众容易共情的元素。
这种对人情和人性的深刻表达,是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它通过构建一个观众能够辨识和体认的世界,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,从而构成了影片成功的基石。
二、神话改写与文化根性:
反抗的多层次性
王霞在讨论中对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文化改写和反抗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,阐明了影片在中国神话宇宙中的创新及其对反抗精神的重新定义。她认为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对传统神话进行了改写,将天选之人的叙事模式进行了颠覆,并融入了个体自由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,体现了中国人“人定胜天”的文化根性。这种改写使得哪吒这个人物更具现代意义,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。例如,哪吒的魔丸设定,原本代表着命运的不可抗拒,但在电影中被转化为个体自由意志的象征,体现了人类对命运的挑战和对自由的渴望。
她还提到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警惕,灵珠化生是中国神话中的独特元素,与西方神话不同,但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对这一元素进行了重大改写。她将这种改写与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中的灵珠化生进行了对比,指出前者具有宗教背景,叛逆行为在森严的儒家秩序下得以化解;而《封神演义》则不同,它是由佛入道的小说,强调天道秩序的残酷和无情。她表示,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天道秩序并不承认不可撼动的先验秩序,而是认为天道与人心相通,可以通过因果和人定胜天的文化根性进行商榷。
王霞进一步分析了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对天选之人的叙事进行的改写。她认为,哪吒的设定原本是一个天选之人的叙事,但影片通过加入魔丸的设定,质疑了天选之人的天生正义感。这种改写直接引发了个体自由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,提升了哪吒的抗争精神到存在主义的层面。她认为,这种改写使得哪吒的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含义,包含了对命运和偏见的双重焦虑。命运的焦虑表现为时间上的紧张感,即哪吒只有三年的寿命;而偏见的焦虑则表现为空间上的进步式成长,即哪吒在社会中的被排斥和自我认知的过程。
三、类型杂糅与叙事创新:
突破传统框架
在学术沙龙上,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片的类型杂糅、叙事结构以及情感驱动力,揭示了影片如何通过突破传统框架,实现了叙事的创新。
首先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并不是单一的类型片,而是多个类型杂糅的产物。虞晓使用《救猫咪》的系统来分析影片的叙事结构,认为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结合了两个主要类型:如愿以偿和反制度化。他解释说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典型的魔法故事,哪吒通过太乙真人的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,太乙真人提供的“魔法”让哪吒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,而不需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影片的后半部分则引入了一个反向的魔法,即天尊施加的穿心咒,这个咒语要求哪吒牺牲自己以救出父母。这两个魔法故事共同构成了哪吒的叙事核心,强调了“成为你自己”的主题。
此外,虞晓表示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还嵌入了反制度化的类型,这种类型常见于枪战和动作片中,讲述了一个人与其集体或团队之间的抗争和博弈。他提到,哪吒、申公豹和敖丙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,他们在面对规则和体系的冲突时选择了反叛。他认为,这种反制度化的叙事模式使得影片具有了更广泛的吸引力。
王霞在讨论中从人物成长、父子关系和师徒关系等角度对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。首先,《哪吒1》和《哪吒2》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显著的区别。《哪吒1》主要讲述了哪吒从出生到遭天劫的过程,这一过程在《封神演义》和1979年的动画片中可能只需几分钟,但在《哪吒1》中被演绎成了一整部电影。她认为,这部影片主要在讲述哪吒的进步式成长,通过视觉化的呈现展示了哪吒的出生和遭天劫的过程。她提到,哪吒的出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,这种围观场面直接导致了偏见的产生。她引用福柯的理论,指出围观是一种先天的视觉暴力,群体对个人的围观伤害了哪吒的社会人格,使得哪吒始终没有群体的归属感。这种感觉在《哪吒2》中得到了延伸,哪吒虽然与底层站在一起,但内心始终没有归属感。
她引用知名学者戴锦华的话,指出“哪吒既是宇宙的中心,又是世界的弃儿”,体现了独生子女的集中特点。她认为,哪吒的父亲李靖对他的爱是有问题的,类似于独生子女一代的父爱问题。李靖的爱表现为“我爱你,我可以为你去死,但我不陪伴你”,这种父爱在《哪吒1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可以说,哪吒的形象实际上是中国30年来独生子女成长中的一个内心画像。
她表示,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不再是垂直的,而是横向的,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父权关系的变化。这种横向关系体现了父亲与儿子的紧密联系,而非传统的垂直权力关系。片中的三对师徒关系代表了跨阶层的流动性,提供了社会结构松动和晋升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一旦被转化为升级打怪的“内卷”制度,就可能成为问题,类似于历史上的科举制。
四、文化符号与社会现象:
言论表达的多样性
四位学者一致认为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现象,更是一个社会现象。影片通过文化符号的使用,反映了大众潜意识和时代精神,成功地捕捉到了当下的社会情绪和青年人的心理状态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在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完成了迁移。影片不仅呼应青年人的迷茫和抚慰需求,还从个体的角度上升到了宏观的层面。哪吒从一个被动的个体成长为一个为天下苍生拼命的英雄,这种转变使得影片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。
左衡在最后的总结中,强调了影片在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。首先,影片中所体现的“中二”心态带有一种悲情色彩,意味着非理性,而这种非理性容易在观众中产生共鸣。他提到,围观是一种暴力,而在现代社会中,很多人渴望被围观,这种现象在影片中也有体现。例如,当哪吒和敖丙共用一个身体时,哪吒将自我视为他者,这种自我观看的方式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。
他说,影片的最终结论可能需要在未来才能出现,因为影片尚未下线,可能会出现更多不同的解读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,不同的人对影片的感受和解读各有不同。最后,他强调了影片在类型杂糅、符号使用和情感表达方面的特点,并鼓励观众通过自己的解读和叙事,进入现代学术的训练思维。这种多角度的解读不仅丰富了对影片的理解,也揭示了影片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深远意义。


